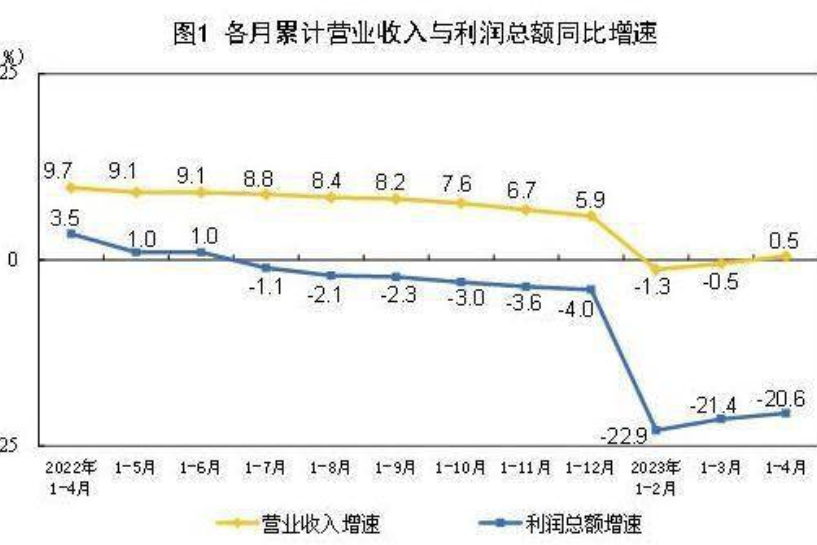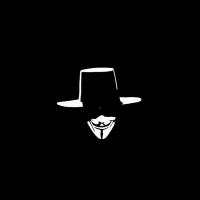2023年4月19日,中国动画教育事业领军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教授与世界级动画艺术家乔治·史威兹格贝尔(Georges Schwizgebel)于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进行了大师对谈。孙立军教授与乔治·史威兹格贝尔就动画艺术创作、高层次动画人才培养、中国动画学派及未来合作方式等话题进行了多维度探讨。
孙立军教授对谈乔治·史威兹格贝尔
Professor Sun Lijun in conversation
with Georges Schwizgebel
孙立军教授(以下简称“孙”):今天非常高兴,我提出在上午与乔治老师进行对谈,主要原因在于乔治老师的艺术成就以及对动画的执着精神令我感动。
Georges Schwizgebel(以下简称“Schwizgebel”):谢谢您的赞美。
孙:乔治老师作为动画学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动画学院的客座教授,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与不解之缘,我也将其看作我的长辈。鉴于乔治老师这几天频繁参加活动,十分辛苦,我们今天就进行一个轻松的访谈,同时将珍贵的影像保存下来,丰富到动画学院的资料库中去。

对话者:孙立军教授
Schwizgebel:很高兴你们能邀请我再次来到中国,追忆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3年的上海,这缘起于早年间在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我与阿达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我作为评委与阿达交流,后来1983年的时候,我有了一次出国的机会,因为我与阿达熟识,所以当时我选择去中国上海,于是在83年的时候我与阿达在上海再次相见。我印象里当时的中国仅有上海在做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差不多总计500人,20多位导演,所以我当时有机会与特伟、钱家俊、王树忱等中国动画导演相识。
孙:在我1984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动画后,85年、86年的时候阿达先生在我们班授课,阿达先生当时边给我们授课边制作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影片,十分辛苦。但谁也没有料到的是,阿达先生在我们的课堂上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享年52岁。乔治先生,您作为阿达先生的好朋友,请您分析一下对阿达的印象,共同追忆阿达。
Schwizgebel:1983年,我来到了复旦大学,在这六个月的学习生活中,我常常给复旦的同学们放映我的影片。事实上在80年代,放映外国影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益于阿达先生的帮助,我才能够在当时展示我自己的影片,才有机会认识更多中国的导演并与其交流,所以当时阿达先生提供给了我很强大的支持与帮助,阿达先生是一位特别好的人。在1982年的时候,我去参加德国的柏林电影节,当时我并不认识阿达,但是阿达的《三个和尚》与我的一部影片均获奖了,我来中国的时候也把他的奖项带给他了。
孙:您差不多一年半左右产出一部动画短片,一直到今天,年已八旬的您还在坚持做动画。那么您最初做动画是在哪一年?在哪里学习动画制作?
Schwizgebel: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艺术院校,最初我是在瑞士学的平面设计,在广告公司工作了5年。当时我常常参与一些电影节,发现自己非常热爱动画片,于是在1970年我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独立制作动画电影。我和当时欧洲的许多同龄人一样,都是自学的,我最开始做动画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为瑞士电视台制作节目开场动画,后来慢慢开始制作独立电影,全程在时间上都是自由的,我们当时没有政府的资助,仅有瑞士电视台和谷歌地图的赞助。而后到80年代的时候,制作动画慢慢变成了我的全职工作。

对话者:乔治·史威兹格贝尔
孙:也就是说从60年到70年20年间从事的是艺术设计,到80年代开始集中于做动画。您最初开始做动画时所用的动画技术是怎样的?当时动画技术还在胶片逐格拍摄的阶段,是您自己在拍还是有摄影师?我们知道当时声音部分的处理要稍复杂,不及当下简单,那么当时的声音和画画,都是您独立完成的吗?
Schwizgebel:在当时,动画制作在我看来是比较简单的,有许多种重复性的工作,我们画了很多的东西,用一个35毫米照相机完成了动画制作。当时我们有一本参考书,书里写了如何画画、如何做动画,我们通过自学,努力研究这本书努力绘制成了动画。刚开始做动画的时候,是我们三个自由职业者一起做,也就是说影片有三个导演。最初我们做的动画就是像电视节目开场动画这种10到20秒的简单的动画制作。后来随着我们的学习,逐渐学会了如何做出故事版等更进一步的动画制作。后来慢慢取得了一些进展,当我终于开始制作我的动画电影时,并没有得到什么投资赞助,以至于我的前三部作品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没有得到任何的资金支持。但好在当时的工作比较好找,我可以去拍广告赚钱,同时还会做任何有钱赚的工作,比如在餐厅洗碗或去别人家里做墙绘。这样的生活长期持续下去让人非常失落,一直到之后瑞士政府开始支持影院发展,这可以称作一个重要事件,再后来,我们团队制作的电影开始在电影节获奖,在当时我们作为一个瑞士团队获得了赞誉,而后慢慢的,动画就成为了我的全职工作。
孙:您后来一直在坚持做动画,有什么动力?在中国,通常艺术影片由高校产出并用于做艺术研究,而您的独立作品几乎全部为艺术短片,您后期的作品是由政府支持还是企业资助去拍摄的?
Schwizgebel: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帮助影片创作的机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只能看到产业化完善的美国影片了。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支持方式,很多在法国、在瑞士的动画短片都做的非常棒,也有很多欧洲的动画电影节可以参与,对动画影片的细分种类也比较细致。在当地电视台也能得到一些机会与支持同国外志同道合的友人共同制作,我们也非常喜欢和国外的人员合作。而现在又出台了新的政策,比如帮助年轻人进行影片制作,比如对制作动画片非常友好的国家加拿大。相对于其他地方,欧洲制作短片的氛围是比较好的。我当时很幸运的地方在于刚开始我的动画生涯就取得了一个“小成功”, 所产出的动画短片数量及完整度都很客观,使得当时的我很容易得到多方的支持,然而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有足够的钱去做自己的动画当然比较困难,所以如果能有另一份工作比较好,比如我当时是同时做着平面设计师赚钱。整体来说,制作短片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需要这些短片,只有电影节需要,但电影节也很难提供资金支持。在当时电视台也不需要这些短片,他们需要剧集以及一些长片,

对谈现场
孙:在短片的前期筹备阶段,如何确定自己的选题?
Schwizgebel:在选题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灵感,比如听音乐或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便会根据从中截取到的某一灵感决定作品的选题。
孙:除了选题之外,在美术风格方面会进行哪些探索?
Schwizgebel:在这些选择下,我更愿意选择自己熟悉的内容与美术风格,但也会去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我会在音乐与运动上进行一些创新尝试。现如今,电脑技术的发展其实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探索的可能性,但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我还是会选择自己熟悉的内容与美术风格去制作。
孙:您作品的动画语言非常独特,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参考?比如用摄影机先拍一些,然后再根据运动进行二次创作。
Schwizgebel:相较于好莱坞的经典动画作品来讲,我更喜欢用非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相较于实拍而言,我作品中的运动更像是一种梦境式的运动,结合具体的片例,我们看到其中的运动和现实的运动并非完全相似。
孙:在动画片的创作中,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实验性的艺术动画,都非常注重音乐的作用,您在创作当中是先有音乐还是先有动画?会选择哪种声音制作的方式?
Schwizgebel:在我将近一半的影片当中,都是先有音乐,而后跟着音乐去制作动画和构思故事的。但是在另一半影片中,我是先做动画的,做好动画后再让作曲家为我的影片去配乐或者挑选一些合适的音乐。如果我们主要的侧重点在于想讲好一个故事,最好是先进行动画制作,而后寻找声音老师为我们的动画进行配乐。
孙:您的作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通常在主题表达上更多的是表现还是批判?
Schwizgebel:对我来说,好的影片应当是将多种元素结合,比如好的故事、好的音乐、好的视觉等。我的作品有时是起源于一个视觉创意,而不是起源于一个故事。将视觉元素与故事、音乐等等其他元素结合表达是十分难做到的事情。而在作品的主题方面,我的作品会与我的生活产生联系,会涉及到一些自我表现内容,表现我自己生活中的故事等,其实每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自我表现,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孙:加拿大有一位伟大的动画家Frédéric BACK,他的代表作《种树的人》获得奥斯卡奖。我和BACK没有见过面,但却有过书信往来。他在信里提到他的作品并非如同迪士尼那般让人产生笑意,他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呼吁年轻观众关爱地球、保护环境。您是否也在影片当中是否有诸如此类的表达愿景?在这几十年的创作当中,是否有一个创作主线?
Schwizgebel:我曾了解过这位加拿大著名的动画导演BACK,非常喜欢他创作的精美影片。但在我的影片中,我更希望表达一些诗意一样的东西,希望给观众提供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世界,所以我的影片当中不一定含有一些教育意义的内容。我的主题中希望有一些诗意的主题让观众观看后感到喜悦,有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导演我很喜欢,Norman McLaren,他用不同的技术拍了很多影片,并且在他的影片当中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我同样也十分欣赏。

对谈现场
孙:在每一部短片当中要画多少张画面?
Schwizgebel:在我的大多数作品当中,可能要画3000-4000张图。但我的某些作品会有一些反复循环的主题,4分钟的话就只有400多张不同的画面,对于循环来说,画图量就会减少。比如“JEU”这部作品所涉及到的循环内容,所需要的画相对来说就较少。
孙:您最新的作品是在电脑上完成的?还是仍用的传统的方式完成的呢?
Schwizgebel:我很少用电脑,原因是最开始数字特效出现时,它并不具备美学上的优势,我认为或许对于动画艺术而言,数字特效没有那么合适,它更适用于游戏及其他有助于其他行业视觉呈现的部分。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喜欢手绘的方式,并不擅长借助电脑进行创作。在我的新影片中,仍为手绘完成,但我做完绘画的部分后需要有人帮我做后期的部分,进行后期角色位置上的调整。

乔治·史威兹贝尔先生夫人在对谈现场
孙:在瑞士还有手绘完成这种动画风格拍摄条件吗?包括洗印条件,逐格摄影机的拍摄。
Schwizgebel:是的,仍有这种逐格拍摄的条件。
孙:这对艺术家来讲是很幸福的,在中国现在这种几乎没有了。我在8、9年前去宫崎骏的工作室时就很好奇,宫崎骏仍在坚持用传统的逐格摄影机,当然另外一面也不得不接受电脑的上色和使用一些三维技术,但是他在拍背景时还是使用逐格摄影机,画在背景上,用数码相机拍摄。他的助手说宫崎先生认为电影是物质的,数码不是物质的,所以他非常不喜欢数字化,那么您对于数字化的看法是怎样的,能否从创作角度继续谈一谈?
Schwizgebel:对于年轻人来说,数字技术是有用的,他们必须了解这些数字技术,因为它每年都在变得越发复杂与多样。数字技术可能不是物质的,也不是实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但它却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可能性,让大家做动画的时候能有更多不同的选择。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使用电脑,是因为我不擅长用电脑,在现在的状态中我会选择做我更喜欢的事情,所以才会选择传统的制作方式。但每当我看到当下数字技术所带来新的呈现时,也会感到非常有趣,数字技术有一些好处在,比如在涉及到动画中的运动时,数字技术可以将运动反应的更真实、更精确。但整体来说,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作品中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想要做什么。
孙:目前中国动画市场很大,进行动画教育院校也有很多,超过300所的动画高校都开设了动画专业。可大部分过多的强调所谓的商业性,而忽略动画本身的艺术价值,对于这件事情,您如何看待?
Schwizgebel:中国的美术有悠久的历史,全世界的动画工作者起初也对中国的美术非常关注,事实证明中国的动画也发展的非常好。在中国动画学派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好的中国动画片,尤其是精彩的动画短片。但距离当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却很少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中看到这样优秀的中国动画短片了。很长时间过去后,近几年,随着院校对于动画的学习,优秀的中国动画短片又出现了,这是一个好现象。
孙:从世界动画发展水平上来讲,中国的动画大致处于何种位置?比如以好莱坞为例的动画商业性、以欧洲等地为例的动画艺术性方面进行判断,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Schwizgebel:在商业电影的角度,我不是特别了解,但从艺术性来说,中国的动画有一个很高的位置。但艺术动画往往只能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看到,在商业层面上来讲,艺术动画的市场是受限的。
孙:对中国艺术动画的创作群体,以及动画博士、硕士、本科的人才培养上,你是否有些建议?
Schwizgebel:像在昂西国际动画节以及其他类别的动画节上,也有过其他的学生和动画从业者与我讨论影片相关的内容,我想就是,当在电影节上获取到一些灵感时,我们或许都会产生一些想法去及时的做一些创作。但整体来看,艺术的创作是还是比较主观的。对于动画的学生们,我认为学习动画的学生不论是处于哪一学习层次,热爱是最重要的,对于现在在做的动画工作要有一份热情存在。

孙立军教授与乔治·史威兹贝尔在动画学院
孙:作为一门辛苦的工作,不热爱很难做出一部好的动画。接下来和乔治老师探讨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中国动画学派”?
Schwizgebel:我认为主要关键词在于“可能性”,中国动画学派未来的发展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对于年轻人的培养,希望他们能够自由的进行创作,最好能够少而精,去热爱他们从事的事业,去学习不同的技术,最后有成果得以向大家展示。

孙立军副校长(左一)李剑平院长(右一)与乔治·史威兹贝尔(右二)及阿达先生雕像
孙:希望有机会在电影学院的美术馆,能够给乔治老师十几部优秀的作品与画稿做一些展览,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第一站是电影学院,在这里让更多热爱动画的学生能看到乔治老师的作品。
Schwizgebel: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感谢您有这样的想法,每当完成一部作品时我都会产出非常多的手稿、画稿,非常开心能够有这样一个展示的机会。
孙:下一步作品准备何时开拍?有一些想法了吗?
Schwizgebel:我已经开始制作新作品了,在今年一月份我刚完成上一部作品时,就开始下一部作品的创作了,也许两年内就能完成。我最新的作品将在下个月在阿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进行展示,而下一步作品灵感则来自于Oscar Wilde,从这位英国作家的视角出发进行创作,但由于现在正处于这部影片的开始阶段,尚且没有故事,所以日后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孙:我们知道乔治老师的作品都是由自己亲自完成的,但同时也想诚挚的邀请乔治老师与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共同完成一部作品,下一部作品是否可以考虑这种方式?
Schwizgebel:20年前在加拿大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未来来到北京呆上1、2个月的时候,可以来到学校进行合作。
孙:一个即兴的想法,有没有可能,乔治老师与其他国际动画届的友人与中国的动画创作者共同做一个主题,您对整体的设计提出一些建议,每一个国家的动画艺术家按照主题的设计做出一个六七分钟的实验动画?
Schwizgebel:这是一个好主意,之前很少有过这样的合作机会,大多是时候还是自己进行创作,即使坐在一个工作室里,也是独立的自由职业者,当然对于动画来说,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对谈合影